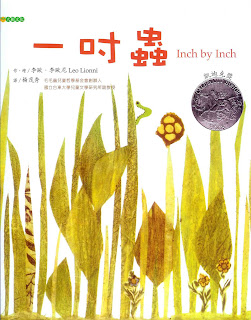文:藍劍虹
友人出去北海岸旅行,行車經過山海邊,轉個彎,乍現火車行駛於鐵軌上。她家小孩Anna很興奮:「看,火車,還有火車條!」「火車條」?什麼「火車條」啊?「就是那個啊。」邊說邊伸著手指向車窗外。大家循著她指的方向看過去,然後,全車的人爆出大笑。「那不是『火車條』,那是『鐵軌』。」哥哥、姐姐嘲笑著她說。
Anna那時小一左右,當然,這不是她第一次發明字詞了。問題來了:當小孩自己發明字詞時,我們該如何?
可以想見地,知道「鐵軌」或「軌道」的人,大都會糾正Anna發明的字詞,並且告訴她正確字詞。不過,可以設想一下,一個和Anna一樣不知道「鐵軌」這個詞的小孩,他會怎樣反應?他或許會想,喔,原來那種東西叫做「火車條」啊。
如果這個設想是可以成立的,那麼「正確字詞」的正確性基礎就會動搖了。一個指涉著某個物體的字詞是怎樣來?或是人是怎樣幫世界萬物取名字?
就從「象」字來考察。中文裡,「象」是個象形字。這表示了,該詞是從大象的外型來取名。不過,不是每一種語言都是依據事物外形來取名。比如,拉丁文中指稱大象的詞有兩個,一個詞義是「喝兩倍水的」,另一個詞義是「有手的」。前一個詞是截取大象超乎尋常的喝水量,後者是觀察到大象的鼻子具有像手一樣的功能。我們也可以想像有一種語言,在那裡,可以截取不同的觀察結果來為大象命名,比如「會搧風的」,那是指稱牠的耳朵,或是「讓地晃起來的」,那可能是來自經驗到象群的奔動。
以上說起來,讓人不免聯想到瞎子摸象,其實也確實如此,每種不同的語言會從大象給人的不同印象、觀察角度來截取出意義進行命名。另個例子:月亮。它在俄語和古波斯文中都有時光的意涵,其詞義是「時光的鏡子」。因為月亮的陰晴圓缺可以用來標記時間,比如我們的陰曆。可是,月亮也有「令人畏懼」或「變幻不定的」的詞義。這怎麼來的呢?月亮是肉眼可見的星體中最令人疑惑的,它會有大小的變化,有時整個消失不見蹤影。月亮主宰著與變幻有關的事務,這源自月亮陰晴圓缺給人的負面感受而來。中文諺語不就有說,「女人初一十五不一樣」,初一十五自然是來自陰曆。人們也常會將月亮與比如法術、巫術相關的事物相聯繫。
「大象」、「月亮」,這是很古老的詞了,兩個指稱物的存在當然是比詞更久遠。可是,我們會碰到新的事物,比如火車,這是跟著現代化、工業化而來的產物,其他的還有電視、電冰箱、電話和電燈等等。新事物出現時,不同的語言也會有不同的造詞方式,比如電話,英文tele-phone,該詞是由「遙遠」和「聲音」相綴而成,中文則是以「電」和「話語」相綴而成:以電波傳送的話語。兩個新詞強調的意思不同,前者強調遠距離,後者則著眼於傳播的介質。
可以看得很清楚,面對新的事物,命名策略和以往並無不同,儘管它會從舊有的辭彙去拼接。可是,一樣可以發現其偏重的語意會不同。
那現在可以來看,同一種語言中對同一種物件的不同名稱。我們知道醫院中透過一組醫療器材給病人補充生理食鹽水或混入藥劑的東西連同其裝置,叫做「吊點滴」。可是,在大陸地區,那叫做「吊水」。聽到有人稱呼這為「吊水」,不免像我們聽到Anna說「火車條」,會令人想發笑。「吊水」,這很奇怪嗎?裡面確實是水,生理食鹽水,也沒有錯啊。該詞著重的是其內容物,不管其成份為何,至少看起來就像是水。吊點滴,則著重該裝置的運作方式給人的直接印象:一點一滴地輸入。
必須說,兩岸用詞上的差異,並非是可以用習慣去解釋,而是必須看到造詞的語意差異。理解了這一點,吊水和吊點滴兩個詞就沒有哪個才是正確的問題。它們都是「正確的」。同理,Anna的「火車條」,也有其造詞依據。
「鐵軌」中「鐵」一字的使用看起來偏重其材質,然而也非正確,因為其材質應該是鋼。鐵也是印象罷了。Anna的造詞依據,沒有針對材質,而是純粹偏重視覺印象,這一點和將鐵作為金屬的印象泛稱也是相同的。
字與詞語的創制
那可以以使用人數多寡來區分正確與否?若以此來說,使用吊水一詞的人肯定比我們多,難道我們也要跟著改用該詞?此外,同樣在台灣,各地也存在著對同一個事物,比如花草或是物種,有不同的名稱,一地的人也不能強要令一地的人改變用詞。同理,某個小學班級中的幾個喜歡玩在一起的小孩,他們可以創制只有他們理解和使用的詞語。甚至可以縮小到只有一個人創制的詞語。個人語言?是的,可以這麼說,那表示了該創詞者給予了一個新的語意角度或是面臨一個新的概念而進行創制新詞。比如詩人的創作或是哲學家乃至學術上的術語。
這甚至應該說是常見,許許多多的詞彙都是少數人或是個人創制出來,而後被公眾所使用。比如,翻譯者,他們是第一個面臨某個來自異國語言的新事物和概念的人,他們就身負以他所隸屬的語言來創制出一個新詞的任務。在東西方文化交匯的時候,許多新詞就這樣被創制出來,比如「社會」一詞,就來自日本學者的創制。現代中文中有太多的詞彙來自日本,作家阿城說,如果將這些詞彙拿掉,那我們都無法開口說話和寫字。
舉個例子,當時李鴻章最痛惡這些進入中文的日本詞彙,常常作檢查批示,指出某某詞是「日本名詞」,可是後來他發現,連「名詞」一字也是日本詞彙,那時他只好放棄這種稽查語詞的工作。
必須確認一個事情:面對新的事物、概念時,人們會進行創制新詞的動作,一個語言社群會如此,一個小孩也是如此,尤其當他面臨著那麼多不勝數的新事物,儘管這些新事物對我們大人來說並非是新事物,不過,這一點其實也不正確,因為大人遺忘了在他小時候,那些熟悉的事物也曾經是新的事物。
下雨花與蜜蜂草
必須脫離那種正確語言的概念和識字卡的教學模式。一位友人轉述,兩位常在野地玩耍的姪女,沒有大人拿著識字卡去教他們所謂的「認識」大自然。在他們經常玩耍的地方有馬櫻丹和蘆葦。他們發現到馬櫻丹的花可以輕易地撒著玩,而蘆葦的種子會隨風飄散,就主動幫這兩種植物命名:前者因為可以抓起一把撒在人家頭上,像下雨,所以被叫做「下雨花」;而後者,因為群聚散揚像蜜蜂成群結隊,叫做「蜜蜂草」。在這個場景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名稱是怎麼被創造出來的:那是由命名者(小孩)和被命名者(植物)的相互關係中誕生出來的,是命名者從這個實質具體的相互關係的主動意識中被給予出來,而非被動地接受他人的告知。
這是一種主動或能動的語言學。相反地,那種總是要求正確語詞和構句的語文教育是被動的語言學,它將語言視為固定、不會演化,更無法去創制、發明的一套系統,使用語言的人僅能被動接受和學習。面對語言的變異性,則是透過一系列的考試和規定試圖來加以規範。這種被動的語文學無視語言的不穩定,並抹煞了文學的可能性。這正是我們當今文學教育所遭遇的問題。
主動的語言學絕非反對語文教育,相反地,是語文教育在反對和壓制能動的語言學。得釐清語文學和文學的衝突差異所在。比如,前面提到的「蜜蜂草」,這是語文學所不容許的字詞,它的正確名稱應該是蘆葦。可是,語文學無法去預測、涵蓋該植物在不同狀況和不同的人相遭逢的無數情狀,比如小孩將之撒揚在風中的遊戲情狀。又,「貓」指稱我們對貓的概念,語文學上,這是名詞。語文學系統會去壓制該詞作為其他詞性的可能,比如,將之作為動詞使用。然而,當代大陸小說家莫言,在小說中寫了某人「貓著腰」。既然可以「貓著腰」,那可不可以來個「牛著做」?
這種壓制會扼殺文學性語言,即一種充滿變易與能動性的語言。《山豬.飛鼠.撒可努》的作者,排灣族作家亞榮隆.撒可努回憶他小時候被壓制的經驗,他的作文總被老師批評為「跳躍式邏輯」、「文藻、辭彙不通」。他要形容滿山水果,寫著「水果多到我的眼睛裝不下」,但是卻因此被嘲笑。事實上,成語「琳琅滿目」中的「滿目」不也使用了同樣的比喻法嗎?
相信如果他當時使用了琳琅滿目來形容,那老師肯定會加以讚賞而非嘲笑。很久以來這種以成語為尚的教學扼殺了不知道多少文學細胞。Anna的哥哥就是如此。他的造句充滿成語,比如:「這家餐廳不但窗明几淨,還有青山綠水的風景和山珍海味的美食,簡直是世外桃源,也因此有口皆碑。」這樣的句子,老師竟給了三顆星的評價。
作文造句中片語「琳琅滿目」的狀況甚至到了「滿目瘡痍」的境地。這說穿了只是為了考試的教學。套語式的表達阻礙了孩子和我們以自己的眼睛去看和以文字去自由表達我們和世界遭逢的各種情狀差異。
當代作家甘耀明在《喪禮的故事》中,就批判了這種以考試為導向的成語教學。那涉及一位不愛讀書的小孩無意間拔了一位乞丐的一根鼻毛,因此神奇地獲得最高分的國文成績。這情節自然是嘲諷祭孔時拔牛毛以求智慧(好成績)。接下來,幾位同樣不喜歡上課的同學蹺課相約再去拔鼻毛。好玩的一個情節在於:乞丐爬樹跑走了,幾位孩子也跟著爬上去找,沒找著,卻從樹上發現到教室外的鄉間山水如此美好。這景緻引得孩子想造句吟詠一番。
一位小孩說:「真沒有想到我們這裡有這麼好的風水。」另一個小孩接著說:「這風水真是好到可以自掘墳墓。」
不知道Anna哥哥的國語老師會給這個成語造句幾顆星?甘耀明借著孩子之口說出了片語教學的自掘墳墓!
藍劍虹
喜歡閱讀很多課外書籍和閱讀小孩;
喜歡將故事當理論閱讀,將理論當故事閱讀;
也喜歡書寫。喜歡畫畫,也教小朋友畫畫。
著有:《以塗鴉對抗填鴨》(人本)、《塗鴉畫冊:放牧的眼睛》(人本)、
《許多孩子·許多月亮》(晴天),編過《劇場事》等。
(刊於《兒童哲學》第5期,2011年5月出刊)